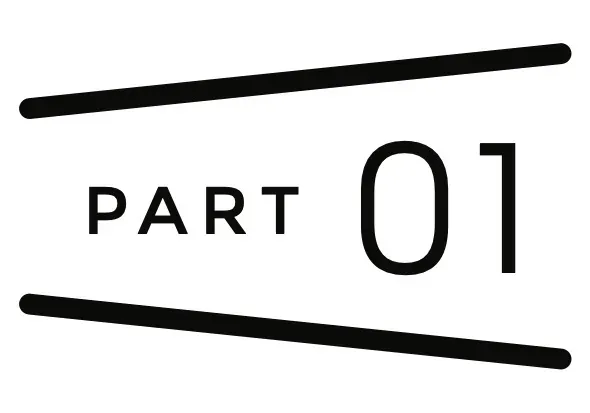
道光十年(1830)的扬州,晨雾总是从运河水面升起,漫过青石码头,钻进埂子街深浅不一的巷陌。谢宏业推开新漆的木门时,那股混合了陈年木料、新鲜米浆与干花香料的独特气息便飘了出来——这可能是他的“谢馥春香粉铺”开张的第三个月。店堂里光线昏暗,几位从老字号“戴春林”请来的老师傅正沉默地工作着。他们的手指在各种原料间移动,动作缓慢精确如呼吸的节律。一位师傅正在制作着产品,他的手掌在瓷盆中画着圆,腕部微微抖动,仿佛在进行某种传承了数代的神秘仪式。墙角处,另一位师傅照看着一排青瓷瓮,瓮里是用上等菜籽油浸泡的玫瑰与茉莉,已在廊下经历了两个月的“日晒夜露”。他每隔三日便会打开瓮盖,用特制的竹器轻轻搅动,让花香与油性更彻底地交融。这一切,都发生在没有温度计、量杯或化学仪器的时代,全凭师傅们指尖的记忆与眼睛的判断。
谢宏业曾是药材铺的学徒,能辨识数百种草本的性味。他相信这些知识同样能用于调配敷面的香粉、润发的头油。此刻,他或许正俯身查看一份刚运来的“材料”。门外,挑着菜担的农人、赶着去书院的学子、坐着青布小轿的女眷陆续经过,几乎无人向这间不起眼的新铺投来一瞥。谢宏业的账本上,第一页记着开张以来的微小收支:购入稻米三石、菜籽油两瓮、各色鲜花若干;售出鸭蛋粉七盒、头油四瓶。最初的店铺难免利润微薄,也许仅够维持店铺日常。他不会知道,他这间倾尽积蓄、仅为传承几门手艺的小铺,将在时间的河流中漂向多么遥远的彼岸;他更不会想到,数十年后,这些盛在青瓷罐或红漆盒里的香粉,将远渡重洋,在旧金山一场名为“巴拿马—太平洋”的万国博览会上,让那些戴着白手套、手持放大镜的金发评判委员们为之颔首,并将一枚闪耀的奖章授予这个来自东方的陌生名字。
几乎在同一时光,巴黎里沃利街四十二号,皮埃尔·娇兰先生刚刚调制完一瓶新的香水。午后的阳光透过高大的玻璃窗,洒在排列整齐的水晶瓶上,折射出细碎的光斑。他的店铺一定比谢宏业的宽敞明亮,橱窗外是奥斯曼男爵改造中的崭新巴黎:宽阔的林荫大道上马车辚辚,穿着鲸骨裙的女士们手持阳伞缓缓走过。娇兰先生也是药剂师出身,他对香料的痴迷源于早年对化学实验的热爱。此刻,他也许正将来自各地的材料按比例混合——他有一本厚厚的笔记本,记录着每一次实验的配方与效果。他的客户名单里包括欧仁妮皇后,他为她特制的“帝王香水”装在水晶雕花的瓶子里,瓶塞上系着丝绸蝴蝶结。东西方关于“美”的商业故事,竟如此相似地从药剂师的研钵与嗅觉开始萌芽。然而轨迹即将分野:在西方,香水将依托新兴的有机化学工业与全球殖民贸易网络,迅速成为一门庞大的、系统化的产业;而在东方,谢宏业的香粉仍将在一段漫长的时间里,依赖老师傅们的指尖温度、本地稻米的品质、扬州城内闺阁女子间口耳相传的声誉,以及那套建立在“手艺”而非“科学”之上的认知体系。
时间如运河水般平静流淌了三十四年。同治三年(1864)的杭州,战争留下的伤痕尚未完全平复,河坊街有些店铺的门板上还残留着刀劈斧砍的印记,石板缝里似乎还能闻到淡淡的焦土气。孙传鸿就在这样的时节挂出了“孔凤春”的招牌。他不像谢宏业那样师出名门,早年挑着货担走街串巷的经历,让他更懂得市井百姓需要什么。他听说太湖边的渔家女常用珍珠粉敷面以抵御水汽,便设法购来品质稍次的碎珍珠,研磨成极细的粉末掺入香粉中。他的“白玉霜”上市后,虽不及名门闺秀所用之品奢华,却在市井女子中颇受欢迎——她们发现这种粉敷在脸上确有清凉之感,且在夏日不易被汗水冲花。后来,经过13道精湛工序打造的鹅蛋粉,不仅是孔凤春的明星产品,更曾在旧时作为富贵人家的嫁妆,见证了无数重要的时刻。
谢馥春与孔凤春,一个在扬州,一个在杭州,像两株安静生长的植物,依靠江南丰沛的雨水与文化滋养,在有限的方圆内开枝散叶。它们的账本上一定会记录着本地主顾的姓氏:某府小姐取走茉莉头油两瓶,某府姨娘订了玫瑰香膏一盒。它们的香气飘散在秦淮画舫与西湖游船之间,尚未与一个叫做“国货”的、充满政治意涵的宏大概念产生关联。
真正的、具有现代意义的转折,发生在世纪之交的光绪二十四年(1898)。那一年,古老的帝国中枢,一场名为“戊戌变法”的革新运动如盛夏疾雨,来得迅猛,去得仓皇,“六君子”的血洒在菜市口的尘埃里,宣告了体制内自上而下温和改良的幻灭。而香港维多利亚港的海风,常年裹挟着咸湿的水汽与码头装卸的喧哗。冯福田——一个曾在怡和洋行做过十年买办、见过蒸汽轮船与电报机的广东人——做出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决定。他将积攒多年的两万银圆,全部投入一处新租赁的厂房。厂房里传来的不是石磨碾米的窸窣,也不是研钵捣花的轻响,而是两台英国产蒸汽引擎驱动着数台压盖机、搅拌罐与灌装线的规律轰鸣。这里是“广生行”,中国第一家采用机器规模化生产化妆品的企业。这里生产的“双妹”牌花露水,装在统一规格的回收玻璃瓶中,贴着用德国石印技术印刷的彩色商标——商标上两个并肩玉立、身着时髦旗袍的少女,面带微笑,眼神望向远方。冯福田在《华字日报》上刊登广告,宣称这是“采用化学工艺,提纯百花精华”的现代产品。他甚至为产品撰写了详细的使用说明:“沐浴后轻拍于身,可避暑气,可祛秽味。”
一九〇三年初春,冯福田乘坐港沪班轮抵达上海。他站在甲板上,望着外滩那些正在拔地而起的欧式建筑,心中已有盘算。三月,广生行上海发行所在南京路正式开业。这个后来被经济史学者标记为中国近代化妆品工业“元年”的事件,在当时并未引起太大轰动,只在《申报》角落有一则百字简讯。然而现代性,确已以一种混合了机器效率、商标法律意识与大众报刊广告的姿态,悄然登陆黄浦江畔。发行所的橱窗里,双妹花露水与雪花膏陈列在红丝绒衬垫上,旁边竖着中英文对照的说明牌。不时有坐着马车的洋人太太或好奇的华人绅士驻足观看。他们或许不知道,这个看似寻常的商业举动,正悄然改变着这个古老国度里“美”的生产与流通方式。
当历史的车轮滚入二十世纪第二个十年,变革的速度骤然加快。宣统三年(1911)深秋,紫禁城的黄昏终于降临,一个绵延两千年的制度就此终结。而在万里之外的德国汉堡,药剂师奥斯卡·特罗普洛维茨与皮肤学家保罗·温塞尔,则在一间弥漫着石炭酸气味的实验室里,成功稳定了一种油与水的混合物。他们发现,在特定比例的乳化剂作用下,油脂能均匀包裹住水分,形成稳定的膏体。他们将这款前所未有的润肤露命名为“妮维雅”(Nivea),拉丁语意为“雪白”。科学的理性之光,开始系统性地照亮人类肌肤护理的微观世界,化妆品与皮肤医学的联姻初露端倪。几乎与此同时,地球的另一端,一九一五年春天的旧金山,为了庆祝巴拿马运河通航,一场荟萃全球物产的万国博览会正如火如荼。中国送展的数千件产品中,获奖之多,不一而足。捷报通过海底电缆传回,举国报刊争相刊登,视为奇耻大辱后难得的扬眉吐气。在长长的获奖名录里,谢馥春的“文雅佩玩香珠”、孔凤春的“白玉霜香粉”、广生行的“双妹粉嫩膏”赫然在列。彼时,谢宏业与孙传鸿的姓氏与商号,因这世界认可的荣光,被第一次写入了超越地方的商业史的更广阔叙事。而当时的民国大总统黎元洪亲笔为双妹题写的“尽态极妍,材美工巧”的八个字,从此超越了对技艺本身的赞美,成为一种微妙的隐喻,暗示着一个民族工业与一个民族国家的集体意识之间,正在历史潮流的推动下,尝试着某种生涩而必然的结合。

一九二八年秋日的某个黄昏,上海南京路先施百货的屋顶花园首次亮起霓虹灯。当电流接通,那些弯曲的玻璃管骤然绽放出魅惑的粉红与幽蓝,将楼下熙攘的人潮笼罩在一片超现实的光晕中。这光芒,如同一个新时代的隐喻,迅速漫溢开来。不到三年,从浙江路到西藏路,整条南京路已成了一条流动的霓虹之河。在这片人造星河的映照下,百货公司橱窗的厚玻璃后,陈列品仿佛获得了生命:旁氏白玉霜的瓷瓶泛着温润的光,双妹花露水的玻璃棱角切割着光线,丹祺(Tangee)唇膏和蜜丝佛陀(Max Factor)口红如一排排微小的士兵整齐列队——在那个战争的年代,女性用口红表达反叛的姿态,象征着拒绝屈服以及勇敢的力量,就像烟草对于男性一样重要。民国才女张爱玲曾在散文《童言无忌》中这样写道:“生平第一次赚钱,是在中学时代,画了一张漫画投到英文《大美晚报》上,报馆里给了我5块钱,我立刻去买了一支小号的丹祺唇膏......”
在这片光影之河中,同时也可以想象到这样的场景:“百雀羚”的深蓝色铁盒像一枚沉静的墨玉,安然躺在永安公司的玻璃柜里。一九三一年,富贝康公司推出这款护肤香脂时,或许并未预料到它将成为一个时代的 Icon。铁盒上的五彩喜鹊栩栩如生,似乎随时会振翅飞入这霓虹夜幕。盒内是洁白莹润的冷霜,用指尖挑起少许,在掌心化开,是典雅的桂花香气,质地细腻而不黏腻。它从永安、先施、新新、大新这四大公司的柜台,迅速流向更广阔的世界:流向静安寺路电影皇后胡蝶的梳妆台,她会在片场休息时,用银质小勺取少许,轻轻按压在因强光照射而略显干燥的脸颊上;流向霞飞坊“金嗓子”周璇的掌心,她在电台录音的间隙,会对着镜子薄薄补上一层,让嗓音的清甜与容颜的润泽相得益彰;甚至,据某些未经证实的传言,它也流向了西摩路宋家府邸的闺阁,与那些来自巴黎或纽约的瓶罐并肩而立。月份牌广告上,烫着水波纹卷发、穿着高衩丝绒旗袍的摩登女郎,巧笑倩兮,手中常持一盒百雀羚,或是一瓶双妹。画家笔下的这些女性形象,肌肤光滑如瓷,眉眼含情,她们身后或许是外滩的天际线,或许是公园的亭台,但手中之物,总是明确的国货品牌。消费与审美,国货身份与都市时尚,在此时此地的上海,达成了一种心照不宣的、精致的共振。
上海已成为这个行业跳动不息的心脏。根据一九三三年上海市的调查,全市专业化妆品工厂已达一百三十余家,大小工场作坊更是不计其数。它们散布在闸北、虹口、南市,机器的轧轧声从清晨持续到深夜。印刷厂的轮转机不停吐出彩色广告画,油墨未干的气息与化妆品本身的芬芳混合在一起,飘散在都市的空气中。这繁荣背后,是完整的产业链初具雏形:有专门供应玻璃瓶的厂家,有生产锡管与铁盒的工场,有代理德国香精、法国染料的洋行,也有在《申报》、《新闻报》上包下固定版面、专营广告的代理公司。这是一个自发形成的、充满活力的生态,尽管其中绝大多数企业规模很小,但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近代化妆品工业的第一个黄金时代。
然而,东方的天际线已经堆积起不祥的乌云。一九三七年八月,淞沪会战的炮火撕裂了黄浦江的宁静,也击碎了霓虹灯构筑的所有幻梦。当时,这样的情形或许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先施公司橱窗的玻璃在爆炸声中碎裂,里面的化妆品散落一地,被匆忙奔跑的脚踩成混杂的泥泞。工厂的机器陆续沉默:闸北的许多小厂在战火中化为瓦砾;广生行的一部分设备艰难拆运内迁至重庆,在防空洞旁坚持着小规模生产;更多的工厂则在物资封锁、原料断绝与恶性通货膨胀中,如缺氧的鱼般艰难喘息。谢馥春的扬州老铺在一次空袭中受损,后院储存香料的库房被震塌,老师傅们抱着抢救出的少许原料,在乡间亲友处暂时躲避。孔凤春的杭州作坊一度完全停产,孙家后人将重要配方与工具埋入后院地下,举家前往金华暂避。对美的追求,在生存的沉重命题前,被迫退到最隐蔽的角落。据说,黑市上,一小盒未被炮火损毁的百雀羚或蝶霜,价格可能等同于一袋面粉。妇女们或许会悄悄用金银首饰去交换,那不仅仅是护肤,更是在废墟与恐惧中,对曾经“正常”生活一丝微弱的维系,对自身尊严一种固执的守护。
一九四五年,战争在世界范围内结束。全球都在废墟上尝试重建,新的秩序与生活方式也在伤痕中孕育。在朝鲜半岛南部,徐成焕用一辆手推车开始沿街贩卖他用山茶花籽榨油、自制的护发油,他的小作坊被命名为“太平洋化学工业社”,谁也不会想到它将成长为爱茉莉太平洋集团。在纽约曼哈顿一栋公寓里,雅诗·兰黛夫人正将她用火熔化、混合了香氛的面霜,小心翼翼地倒入一个个精美的玻璃罐,她可能打算第二天去萨克斯第五大道百货公司,向那些挑剔的买手们展示她的作品。在巴黎蒙田大道三十号,一度穷困潦倒的克里斯汀·迪奥,在棉布上画出了那条腰身纤细、裙摆如花朵般铺展的“新风貌”连衣裙草图,它不仅将重新定义战后女性的优雅形象,更将带动整个高级时装与配套美妆产业的全面复兴。世界的化妆品产业,在和平的期许与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中,准备迎接一个全新的、消费主义即将蓬勃兴起的时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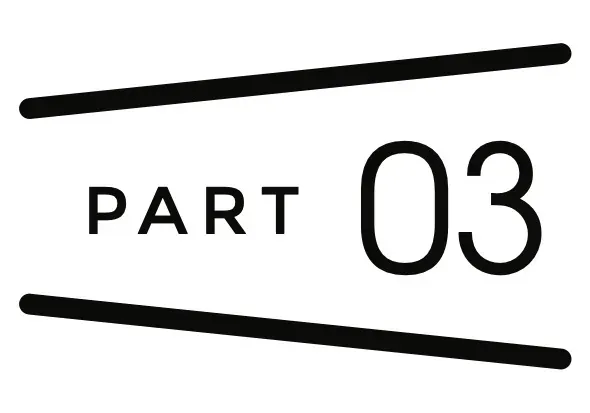
中国的故事,在二十世纪中叶,转向了另一个深沉而复杂的方向。一九五二年的上海,公私合营的红色标语贴满了大街小巷,敲锣打鼓的报喜队穿梭于弄堂之间。广生行——那家曾率先引入蒸汽引擎、在报刊上登载摩登广告的企业——与上海明星香水厂、东方化学工业社等合并,组建为“上海明星家用化学品制造厂”。南京东路上原广生行气派的发行所,挂上了崭新的厂牌。曾经在市场上自由竞争、各显神通的品牌,被陆续纳入国家计划的庞大体系之中。“双妹”、“明星”、“友谊”这些承载着数十年商业记忆与消费者情感的商标依然存在,但它们的意义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它们不再代表某个特定厂家的品质承诺或美学追求,而是成为计划经济蓝图中,一类产品的标准化代号。
位于上海桃浦的新建厂房里,流水线按照年度生产计划运行。雪花膏、花露水、蛤蜊油是三大主力产品。配方被统一、简化,以实现最大的产量与最低的成本。以上海家化(由明星厂发展而来)生产的“友谊”雪花膏为例:它被装进朴素的白玉色瓷瓶,瓶口用一层蜡纸覆盖,再以铁盖旋紧。香气是统一的、略带甜腻的花香,质地比从前的产品略显厚重。它们不再通过广告或精美的橱窗吸引顾客,而是通过遍布全国的百货公司、供销合作社的网络,按照计划调拨的数量,出现在简陋的玻璃柜台里。价格由物价部门统一规定,数年不变。在上海,一盒“友谊”雪花膏售价两角七分,一瓶“明星”花露水售价三角五分。在北方农村的代销点,它们可能是唯一的护肤选择。
在那个崇尚朴素、节俭与集体主义精神的年代,一盒雪花膏承载的意涵远超其物理属性。它可能是一个纺织女工在被评为“先进生产者”后获得的奖品;可能是新婚夫妇凭结婚证才能购买到的稀缺商品之一;也可能是母亲攒了数月零钱,在女儿离家下乡插队前,悄悄塞进行李的牵挂。美的概念被彻底重构:鲜艳的口红被视为“资产阶级情调”,繁复的护肤步骤是“追求享乐”。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整齐划一的审美观——健康的红润肤色、整洁的仪容、朴素的着装。化妆品的功能被简化为“保护皮肤,讲究卫生”。上海家化的实验室里,工程师们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如何提高油脂的乳化效率、延长产品的保质期、寻找更廉价的天然香料替代品。市场的概念、品牌的差异化竞争、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这些词汇已从技术人员的日常话语中淡出。
与此同时,外部世界的产业浪潮正以惊人的速度演进。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西方青年反叛文化与女性解放运动催生了色彩大胆、风格叛逆的彩妆。跨国集团如欧莱雅、宝洁等通过全球收购与市场扩张,建立起庞大的商业帝国。而绝大多数中国普通人的妆台与外部世界的潮流趋势暂时隔绝。偶尔,通过少数的涉外宾馆、归国华侨的馈赠、或被精心剪裁的内部参考影片,一些都市青年得以窥见外部世界的斑斓一角。某些研发人员或许能从有限的进口学术期刊上读到最新研究,但在当时的产业环境下,这些前沿知识很难迅速转化为可供大众消费的产品。中国的化妆品工业,在计划经济的轨道上,度过了近三十年的缓慢运行与一言难尽的时光,仿佛一条冰封的河流,内在的动能仍在,却等待着解冻的春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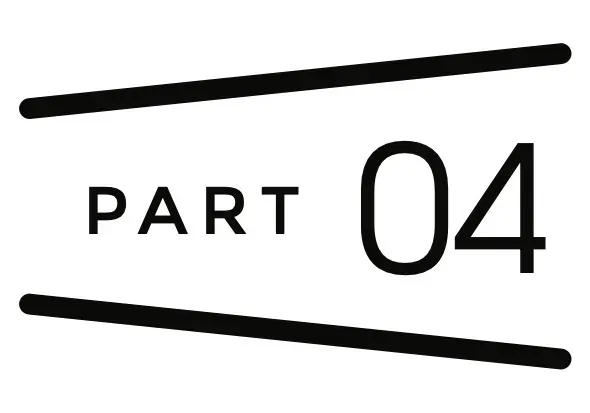
一九七八年的春天,解冻的迹象从细微处开始。最初是气息,是声音,是影像。上海华侨商店的橱窗里,开始出现包装精美的进口护肤品,需要外汇券才能购买,柜台前总是围着好奇的人群。少数对外开放的酒店,闭路电视里播放着日本资生堂的广告短片,模特细腻光洁的肌肤令人惊叹。香港亲戚寄来的杂志,被年轻女子们私下传阅,上面模特的口红色彩是如此鲜艳夺目,与国内流行的单调色号截然不同。嗅觉敏锐的上海家化,将诞生于1962年的 “美加净”品牌重新焕新:生产线空前巨大,被誉为“中国化妆品第一品牌”——身兼创造中国化妆品市场第一支定型摩丝、第一支防晒霜、第一支定型护手霜等无数光荣的民族品牌。1990年,美加净进入巅峰期,以百分之十几的市场份额无可争议地成为行业的第一品牌,年增长率高达两位数。美加净香波的市场份额也接近20%,销售收入为3亿多元。
但接下来,借助中外合资热潮,上海家化在政府招商引资的指令下,与美国庄臣公司合资成立了露美庄臣有限公司。然而合资后由于经营不善,露美、美加净这两个曾经著名的品牌,市场声誉逐年下降。
这个时期——整个一九九〇年代,也是国际大牌在中国市场驰骋的时代——随着国门进一步打开,宝洁的海飞丝、飘柔广告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反复播放;联合利华的力士香皂请来国际影星代言;欧莱雅集团将巴黎欧莱雅品牌引入中国,其专柜迅速占领各大城市最高端的商场。这些国际巨头不仅是来销售产品,更是带来了一套完整的商业体系:它们建立研发中心,分析中国消费者的肤质数据;它们铺设深入县镇的销售网络;它们用饱和的广告投放和精致的视觉形象,重塑着中国消费者对“美”的认知标准。本土品牌在资金、技术、品牌影响力全面落后的困境中,节节败退。许多曾经辉煌的老字号消亡,不少企业沦为国际品牌的代工厂,在产业链的底端依靠微薄利润挣扎。市场似乎给出了残酷的结论:唯有彻底模仿西方,才能生存。
然而,危机中也孕育着痛苦的反思与转机。一些本土企业开始追问:单纯的模仿是否真的有未来?我们是否永远只能是潮流的追随者?正是在这种背景下,1994年,上海家化出巨资回购露美和美加净,并且经过不懈努力,美加净在1997年又重新被评为上海市著名商标,1998年美加净获得了“中国驰名商标”称号。1998年,上海家化又推出了后来被视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品牌——“佰草集”。它不再刻意模仿西方品牌的命名方式与包装风格,其名字取自“神农尝百草”,倡导“美自根源养有方”的理念,是国内第一代将中医中草药理念融入现代护肤体系的先锋品牌。尽管有过迷茫和低谷期,但自创立伊始,佰草集便立下愿景:要让东方本草的智慧,在当代科技中重焕光芒。在2025年这一年,佰草集才让那一抹惊艳千年的“中国白”在现代东方女性的肌肤上焕醒。
值得中国民族美妆产业雀跃的是,上海家化2004年化妆品全国销售额为22亿元,仅次于国际巨头宝洁和欧莱雅,其中高端品牌首次占到公司化妆品总销售额的六分之一。2005年,上海家化携手全球奢侈品零售巨头丝芙兰,在上海开出“丝芙兰—家化”高档化妆品专卖店。此举标志着我国本土企业的“中国概念”站在了世界化妆品市场的前沿……
进入二十一世纪,变革的引擎被互联网技术彻底点燃并加速。二〇〇三年淘宝网成立,二〇〇四年京东涉足电商,购买渠道发生了根本性革命。随后,博客、微博、特别是二〇一三年后兴起的小红书、微信公号、抖音等平台,彻底重塑了品牌与消费者沟通、口碑传播乃至产品研发的方式。新一代消费者在屏幕前成长,他们获取信息的途径空前多元、碎片而直接。他们对品牌的虔诚度下降,对产品成分、功效原理、背后文化内涵的探究欲空前上升。他们熟练地查看美妆博主的测评视频,在社交平台搜索各种成分关键词,在评论区交流使用心得。他们不再盲目崇拜“进口”二字的光环,反而对国货的品质、创新的设计以及能与自身的文化身份产生共鸣的品牌故事,抱有越来越大的兴趣与信任。“成分党”与“文化自信”的消费群体正在重叠、壮大。
资本市场敏锐地捕捉到了这股强劲的潮流。风险投资与私募股权基金大量涌入美妆赛道。新品牌如雨后春笋般诞生,它们生于线上,长于社交平台,深谙与年轻消费者对话的语言和节奏。完美日记通过海量的社交媒体KOL合作、快速迭代的彩妆系列与极具竞争力的价格,在短短数年内实现爆发式增长。花西子则以极其精致的雕花口红、融合古典元素的包装设计以及“东方彩妆”的清晰定位脱颖而出,其“苗族印象”系列产品更将非遗技艺与现代彩妆结合,引发了现象级的讨论(包括傣族印象系列和蒙古族印象)。还有谷雨、林清轩等,不一而足。这些品牌不像传统企业那样经历漫长的渠道铺设过程,它们通过线上平台和各种“种草”直接触达千万消费者,通过及时反馈快速调整产品,形成了迥异于过去的生长模式。
与此同时,那些沉睡多年的老字号,也在新世纪的晨光与“国潮”的浩荡东风中觉醒。比如,百雀羚、谢馥春、孔凤春等都开始了焕发新生。传统不再是需要遮掩的包袱或仅供怀旧的符号,而是可以深入挖掘、进行创造性转化的文化矿藏与信任基石。“国潮”二字,成为连接历史与当下、商业创新与民族情感的关键词。其中,百雀羚与故宫文化的IP联姻,被业界称道。在2025年这一年的两者联创,不仅标志着百雀羚限定版“灵玉”系列包装及礼盒的全新上市,更代表着品牌在高端化、价值符号化以及商业模式升级方面的深度探索。通过“文化共创+商业落地”的双重创新,百雀羚为国内美妆行业树立了一个崭新的价值升级典范。
行业的格局,在看似平静的水面下,发生着深刻而不可逆的位移。竞争的焦点,从营销战、渠道战,逐渐转向研发与科技创新的硬实力。拥有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的上海家化,汇聚上海交大附属瑞金医院于2003年联合研制玉泽品牌,在皮肤屏障修护领域建立起专业口碑。珀莱雅与与国外科研机构合作成立珀莱雅海洋护肤研究中心等,并将“泡泡面膜”等剂型创新产品打造成现象级爆款。薇诺娜则作为中国首个通过临床验证的皮肤学级护肤品,始终聚焦在前沿皮肤科学研究,专注于敏感肌护肤的医学研究,在细分领域构筑起极高的专业壁垒。华熙生物则凭借着在透明质酸产业的全球龙头地位的优势与复用能力,已经构建起了从糖生物学到细胞生物学再到再生医学的全链路产业生态优势,已经成为国际化的生物材料公司和生物活性物公司。本土品牌不再仅仅在营销概念和渠道模式上创新,更开始向产业链的上游、向核心的基础研究与原料创新迈进。它们上市融资,引入国际人才,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尖端科技进行合作。根据专利数据库的统计,自二零一五年起,中国化妆品相关的专利申请量已连续多年位居世界前列。
最具象征意义的行业事件之一,或许发生在二零二三年一个平凡的秋日。当季度的财务报告陆续发布后,一份对比数据引起了财经界与产业界的广泛关注:成立于二零零三年的珀莱雅,其单季总营收首次超越了一二六年历史的上海家化。这绝不仅仅是一个冰冷的财务数字的超越,它是一个强烈的时代隐喻与象征。上海家化,如同一位阅历深厚、血脉中流淌着从广生行、双妹、美加净到佰草集全部历史基因的耆宿,它见证了手工业的温情、民族工业的挣扎、计划经济的规训与市场经济的重生。而珀莱雅以及完美日记、花西子、薇诺娜、谷雨、林清轩等所代表的新生力量,则像一个敏捷、好奇、生于市场经济的深海、长于数字时代浪尖的青年,没有历史包袱。
这种暂时的交替,并非简单的取代或颠覆,而是一条文明长河在奔流不息中必然的经历。旧的河床塑造了水流的方向与底蕴,而新的水流又在不断冲刷、拓宽乃至改道着河的边界,注入新的活力与可能。但与此同时,旧的励精图治后也会接着成为“新的”,而新的如果倦怠不前也会接着成为“旧的”。
商业的世界里,新旧从不是永恒不变的,更是不停地循环和接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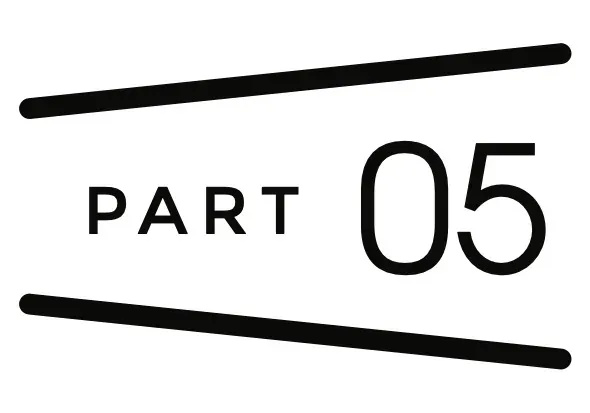
从一八三〇年扬州清晨那间飘散着米粉与花香、依赖老师傅指尖温度的小铺,到今天遍布北京、上海、杭州、广州的研发中心里,精密仪器分析着活性成分的浓度与透皮吸收率;从孙传鸿在杭州河坊街用太湖珍珠粉创制的“白玉霜”,到如今利用萃取技术从高山植物中获取稀有精华;从冯福田在香港引入机器机生产“双妹”产品,到如今全自动的绿色、智能工厂里机械臂将产品精准放入快递盒,准备发往千里之外的直播间消费者手中;从原来传统的日化产品到成为如今的已经融合多个学科的美丽健康产业,化妆品行业早已“脱胎换骨”,中国美妆市场规模自2023年开始已经连续多年超万亿,成为全球第一大消费国别市场,而国货美妆的市场份额早已超越外资,2025年更是高达57%以上——这两百年的旅程,迂回曲折,跌宕起伏,充满断裂与延续、失落与重生。
从19世纪上半叶至今,在两百年的历史激荡中,中国化妆品工业近代史跨越了清末、北洋政府、南京民国政府和新中国成立初期,历经舶来品传入,本土工业萌芽、发展、繁荣、萧条,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周期。而中国化妆品工业真正的现代化历程则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的模仿阶段,到20世纪末和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中国本土民族品牌如雨春笋般的出现与争相进入中国的跨国品牌的竞合阶段,并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迎来了行业发展的黄金十年,以及在21世纪第三个十年开始之初,国货美妆逐渐反超外资品牌,神州大地上再次兴起了“国货运动”。时间粗略算来,总有四十余年。
这无疑是一部微缩的、却极其丰富的产业史诗,其间清晰可见:传统手艺面对现代机器时的执着、调整与融合;民族工业在全球化浪潮席卷下的焦虑、学习、抵抗与进取;民族的审美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暂时失落、重新发现与创造性转化……
历史的激荡永无休止,产业的故事仍在继续。因为,这早已不仅仅是一部关于香粉、膏霜、口红、香水的商业编年史,更是一面清晰而多棱的镜子,深刻地映照出中国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从封闭走向开放、从贫弱走向富强的历史进程中,那些关于“美”的观念变迁、关于生活理想的更迭、关于文化认同的纠结与重塑,以及关于国家产业能力与商业文明崛起的壮阔史诗。
春潮涌动,美力繁花;四十不惑,历久弥新。到了二十一世纪第三个十年开始之际,中国美妆的这条大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奔流不息,而且也将迎来了其发展的黄金时代。
(本文由庄襄平策划、整理与撰写,并辅助使用了Ai大模型。如有偏差或疏漏之处,请以实际情况为准。中国香妆融媒体发布本文只是为了传递更多的讯息,不代表任何有倾向性的投资意见或市场暗示,仅供行业参考。)
合作 laoduoyuya|头图来源 Pixabay.com